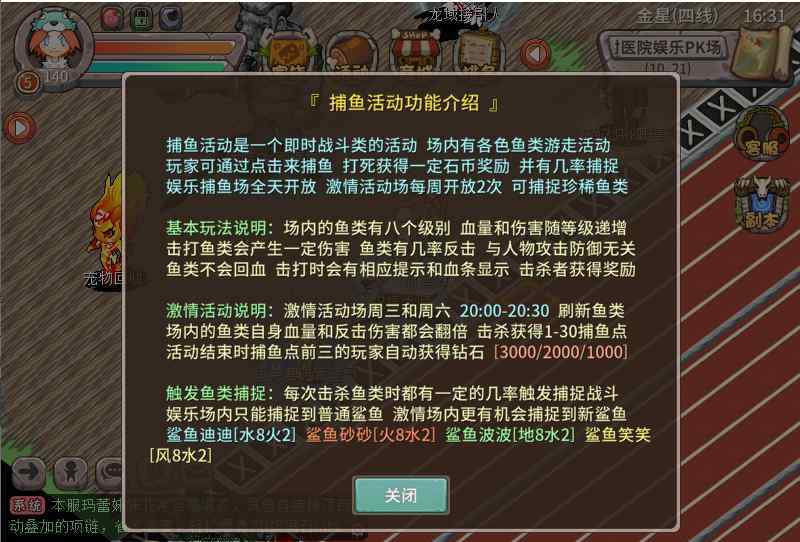北京宋庆龄故居南楼曾是纳兰性德求学的地方。
《红楼梦》被乾隆命名为“明珠家事”,大观园曾被什刹海称为纳兰府。大观园是否真的有自己的园林,至今仍有争论,但清代“国初第一词人”纳兰性德作为贾宝玉的原型一直流传下来,但并不是一个追赶者——毕竟他所建的“野彩湖无分”的沁水亭确实存在过,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作为纳兰性德的朋友,也曾在其间游过泳。300多年过去了,沁水亭消失了,它的地址被后人争论不休,就像早逝的纳兰在北京留下了雪泥的印记。
纳兰之家:它不是世界上的一朵富贵花
纳兰《采桑子·唱雪花》诗中的名句“没有根没有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”,其实挺“傲娇”的。他在华府长大,确实有“傲娇”的资本:父亲明珠是康熙朝的重臣,家道兴旺,正如纳兰所说,“尘京,乌衣门”;我是康熙十年进的商学院,考上之后第二年就考上了。康熙十二年,我因感冒病错过了宫廷考试。生病的时候写了《沁水亭杂识》。我参与了首都的名胜古迹、用兵之思、科学之用、歌舞之美、情侣之词等等,甚至记录了盛世之初贵公子意气风发的身影——纳兰亲口说“德国也疯狂生耳”。
《沁水亭杂识》中的沁水亭,应该是康熙十二年前修建的,它的名字来源于亭所在的水与昆明湖是同一个水系。纳兰曾写过《秋千索》《水亭春望》《仙女》《水亭秋夜》等多首诗,记录了其清新秀丽的景色。至于展馆在哪里,学术界众说纷纭。沁水阁在纳兰府,也就是日后宋庆龄在海北岩46号的故居。
民国学者张认为沁水亭在纳兰府。公园里有一个伯恩馆。淳太子家的儿子溥任,验证了纳兰设计建造了沁水阁。他的弟弟受周启维的诗《伯恩流得远,使龚铭更出名》的启发,改名为伯恩亭。后来经成太子永训修缮,即在当年纳兰宴宾客朋友聚会的沁水阁内建伯恩阁。

宋庆龄故居曾是纳兰府伯恩馆。
在这个“一江村画清图”的沁水亭里,纳兰写诗作诗,研究经史,写了一本书说,在这里,他交出的是“清秀异绝,名为天下败者”——顾贞观、、朱彝尊、颜、梁、江...他们忘了和纳兰多交朋友,顾贞观40。康熙十七年正月,康熙皇帝给博学的儒家家族签了一封信,应该邀请的学者们在北京聚集了一会儿。石、王绾、、朱彝尊、毛、周清源等近百人,或登或访纳兰府,甚至明珠父子五年奔走,将顾贞观的好友从宁古塔救出。张在《清纳兰先生性德年谱》中写道:“凡到京师迷了路者,必自访自慰;并邀请他回家,每次他都不忍辞职;有时差,书和诗经常发。”戴着绣花王冠的满族贵族和落魄的汉族文人经常在溧水亭谈论此事,他们无拘无束。“青川虽薄,而它总是送到名人那里;浓墨重彩的笔简瑶,每一次怜悯都赢得了奖赏,消除了地位的悬殊,使这些真挚的友谊成为17世纪中国文坛上最好的故事。
今天的宋庆龄故居还在湖塘碧波附近。虽然伯恩馆已经翻新,但人们很难回忆起文化沙龙里名人学者聚会的优雅场景,但纳兰读书处、公园里位于南湖南边的南楼和湖边的楼前,纳兰自己种的夜宵花树还在——这棵树也是《红楼梦》里黛玉湘云秋夜唱的东西——在这里,适合做一棵

宋庆龄故居,是纳兰府的南湖。
桑榆山庄:生活轻松又艰难
纳兰之家也是纳兰夫妇赌书倒茶的地方,情话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。他曾写过《浣溪沙,谁独读西风凉》,回忆夫妻生活,“只知当时之道是常事”。20岁时,纳兰娶了两广总督卢星祖的女儿卢氏为妻。婚后,他们住在北京西郊海淀镇南明珠建的桑榆学校。直到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陆病逝,纳兰才于六月写下《蓝湿哀》,成为纳兰词日后诸多“哀情”作品的开端;在这些用鲁的原作所写的诗中,我的姨太太沈婉和许多暧昧女子的相思、失恋、爱而不丧,尤其是“人生若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”在白玉兰玲的仿古拒词中最为著名。
鲁死后,暂时无法进入祖坟,灵柩暂葬双林寺。如今,双林寺只有塔基的遗迹,就在紫竹院公园南门;纳兰曾写过《江南苏双林寺的回忆》,只写了情怀却没有看到场景:“风雨消磨生死之别,似曾相识只是寂寞,情却不能醒。抖在身后,吹得那声可闻”,由此可见爱的深度。

市民跳舞的紫竹院公园南门,据说是双林寺旧址。
双林寺以北不远的桑峪山庄留下的亲情,不仅仅是爱情,更是友情。珍珠在玉泉山宫重建。同时,它建在“甘甜的水和肥沃的土壤和平地上的泉水”的家园里。因此,它靠近玉泉山。长春花园建成前,康熙皇帝在玉泉山宫景明花园听政,方便明珠上朝,成为纳兰府到枣家屯别墅的中转站。就纳兰而言,他的朋友都不是明珠系的高材生,很难频繁出入豪宅交友享乐,而桑榆山庄自然成为不错的选择。
如今双榆树地区高楼林立,与桑榆山庄谐音,但在300多年前,还是颇有新意的——纳兰的诗《桑榆山庄与夜望梁汾》中写道:“登楼时,可垂见,苍翠无边。所有的鸟都不见了,但是牛羊在烟雾中。不知道寺庙是哪一年,钟帆低头一看。见村火无月,有时闻天香。”纳兰说“中畈”不空,桑峪山庄东北有富宝寺,北有现在不为人知、无迹可寻的古清真寺,南有霍克基、曼居基;东南的武塔寺,即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,从东到西与双林寺所在的紫竹院公园相对。里面有纳兰性德的墓志铭,但字迹磨损严重。这里还坐落着海淀上庄的东岳庙,这里曾是纳兰族庙,“重建雨荷乡东岳宫碑”。
有人说沁水阁位于桑榆山庄。其实它的建设时间不一样,但还是纳兰交友的好地方。据记载,这里有庭院和回廊,广泛种植槐树、桐树和竹子,尤其是桑树;还有一座三层小楼——纳兰去世后,顾贞观写下《十指不归河》并注明:“忆桑榆山庄有一座三层小楼,容若和于希年在月亮上玩去云梯,半夜互相倾诉。”还有一个花草堂,作用类似里水亭: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五,纳兰与朱彝尊、、颜、顾贞观、江淹,
桑榆山庄记录了感情,但更悲剧的是。清朝初期,北京的汉族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,所以在聚会上越是忘我,越是感到离别,这成为纳兰交友时无法逃脱的命运。他在《大岙送梁汾》《水龙吟送孙友南归》《潇湘雨露送西归慈溪》中写下了离别的深情厚谊,他的“朋友圈”还合作了一副“浣溪沙野餐对联”:
出郭,春与春已停,东风不冷,故青村有数曲归西山。
不为路发愁,不看花,不喝上一杯清闲,活着不容易。
这个字是在何时何地写的,无从考证,但纳兰的心里充满了“情感”的悲凉情绪,但他看着它。
纳兰死后,桑峪山庄逐渐成为废园和墓地,其母亲罗氏、妾燕、长子福格、孙子詹岱等暂葬于此。经过多年的冲刷,终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后勤服务中心西北侧的老校医院,也是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和当代商场的所在地。还有与纳兰族有关的羊、马等残缺石像,很少有人在意。只有周作人的记录还在纸上——1926年燕京大学迁至海淀,作为客座教授,他记录了上学的路:“假设他早上8点出门,行程如下,即高梁桥15分钟,磁县庙5分钟,白象安南村10分钟,叶赫那拉氏墓10分钟,黄庄5分钟,海淀楼头桥15分钟”——叶赫那拉氏墓,原名

人大校园里的石头文物
来自怡园:休寻遗言之年
与其他关于卢水阁位置的假说相比,乾隆时期太仆寺观的清戴露把“卢水阁是容若的书馆,在玉泉山脚下”描述为最不可靠的——纳兰在玉泉山附近的别墅是从他死后几年才建成的怡园中来的,现在属于圆明园。纳兰虽从未从怡园见过,但对西山一带却十分熟悉——康熙十五年进宫考试第七名,出生后被赐进士为侍卫。“他从南海子、西苑、沙河、西山、汤泉游历,西尝五盘,北尝一五路山,关尝五拉,东南尝太岱,尝奎里。虽然他在尊崇他之前,立刻欣赏了边塞和江南的各种风景,但这也让他“总是想着山中的鱼和鸟”,他总是因为年轻时在卫兵和乡绅中游荡而忧心忡忡。
纳兰的仕途无非是待在殿前,开着车到处走;对其他人来说,在宫廷获得荣誉是美好事业的开始,而对他来说,这是幸福生活和自由气质的结束。颜在《若记序》中记载,他“执勤、巡逻,总在陈宝的尾巴之间。没有什么是平的,日子也没有退休,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。而且看它的意思,有一种对表演的担心,看到任何一个是近臣的人都很尴尬。”在纳兰词《秦怡娥》中,“我想把笑声从绳索中放逐,但又情不自禁地对着镜子”,在《浣溪沙习惯于担心世界末日》中,“工作的人只能一辈子休息”等词。,可以看出在心情上对乡绅的职业感到厌倦。
康熙二十一年二月,纳兰以永陵、涪陵、昭陵之名告祭,二十三日出关,期间作长相思:
山骑,水骑,走向关羽,夜灯。
风越来越大,雪越来越大,所以家乡不能做梦,家乡没有这样的声音。
“夜千灯”这句话被王国维誉为“千古雄奇”。的确,纳兰词的边塞怀古诗脱去了小爱的忧郁面容,呈现出可与稼轩诗相媲美的壮美与萧条。在自驾秋猎的巡游中,在车如流水的马如龙行列中,他看到了“落叶满溪冰,夕阳分外照长短亭”的没落,看到了“冷月悲,西风千里,海为沙”的悲哀,看到了“冰川在大河中流淌”的无奈与孤独, 而苍茫的哀愁”,更有甚者,“大漠风雨,寒烟小草渐消,山河皆乐。 一次又一次的风吹雨打,到处都是荒凉凄凉的风景,思绪无边无际,苍凉无比。所以,除了眼睛里汇集的黄沙白草和凉水恶山,还有心底深处的‘栖居与苦难’的压抑。”他悼念古今十三陵兴衰:“马望青山,故散而盛。然后,斩断烟衰草,认青苔碑碑文。当年休找话,只流了愁秋泪。明十三陵下,我要去新丰打猎。”在繁华的再续前缘,他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惆怅。

海淀上庄的夏日风景
皂家屯:这个时候,我相对忘词了
海淀上庄的南沙河与上庄水库相连,河道宽阔,湖面宽阔,道路两旁都是河流和池塘,枣家屯空的乡村冷清静谧,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纳兰家被赐地时的景色。
有人说沁水阁在枣家屯,不算追赶。纳兰家在这里有一栋别墅。纳兰的《郊区花园是东西》说:“带一对情侣,在石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,很懒。土地要与射击场相邻,花不碍球场”——射击场、球场、花园、石桥,纳兰“会在城里玩”。只是别墅和花园早就没了,只剩下养老院“纳兰花园”西侧的一个小四合院。正门开在养老院停车场的纳兰兴德历史遗址展厅。院子里有一座一米多高的纳兰坐像。戴官帽,穿袍,喝茶,可惜坐像比例太成问题,纳兰也没那么老;所以在参观其背后小展厅的传记资料、书籍和字画时,最好将脑海中的坐姿形象抹去,代入羽生结弦,比如说,让它有一点“公子独一无二”的味道。

在海淀上庄纳兰兴德事迹陈列馆,院内有一幅不协调的纳兰画像。
展厅内还有一个纳兰墓的印章盖,相对完整,证实了早家屯作为家族祖居的历史,这里埋葬着明珠、纳兰三兄弟及其妻儿。

海淀上庄纳兰性德事迹展有纳兰性德墓志铭封皮。
枣家屯纳兰的遗存很少。现在,大多数游客来这里钓鱼,独自享受农舍。如果你想感受一下1930年没有去过纳兰墓,可以写下张任政在“秋风吹诗人之地,肠子断皂荚村”中看到的荒凉景象,只在展厅以北几公里的永泰庄。在这里,墙壁倒塌,房屋倒塌,杂草蔓延,地面堆满了碎砖碎瓦。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,游人的足迹寥寥无几,在风雨和阳光下无声无息,为纳兰性德的故事作出荒凉孤证。

在海淀上庄东岳庙的正殿上,展岱的大门清晰可见。东岳庙曾作为纳兰的宗祠和家庙。
看着北京纳兰的各种“痕迹”,我觉得沁水亭就在纳兰府:陈维崧的《沁水亭观荷》说“江南一景清,恰好在凤城深处”,意思是在北京;纳兰自己在《沁水亭夜宴集诗序》中说:“赐家如近三,日近五。墙壁是刺绣的,被云包围着;门远眺银塘,烟浪漫过。焦滩有雾,晴分太液池淡;他清,崔写风景和山色。.....如果你坐在法庭前,你会有房子的想法;悠闲地看看屋外,自动想到飘回家。”虽然可能有复杂微妙的政治因素,但在沁水亭举行的那些大型聚会,仍可与魏晋竹林七贤、东晋兰亭展、六朝黑衣游、明清云聚相提并论,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
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,纳兰因感冒病逝,年仅三十岁。去世前七天,他在沁水亭举行宴会。"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名人聚集在一起,宫廷的树木被歌唱。""舞台前两天晚上,华容涂上了枝叶."《夜花》成了他的绝唱。
纳兰很远,只留下沁水亭旁明亮开放的夜花树。纳兰族一直住在后海岸边,直到乾隆五十五年,明珠四世孙承安被判盗窃家财。几年后,乾隆将此房赐给成太子永训,并传至同治年间,其后裔禹辈即成为贝子。光绪十四年,嗜酒如命的太子奕譞升任西便门太平湖府“潜龙府”,慈禧将贝子于霞府赐奕譞为新府。载沣攻爵后,新中国成立后,府邸内的房屋全部卖给了隶属于重工业部的高级工业学校。1963年,宋庆龄搬到这里,生活了18年。

海淀上庄东岳庙正殿
名声与拒绝,为爱求情,所遇与所求的深刻矛盾,让纳兰写出了最具情感的作品《画堂春》:“一代一对,争教,两忘我。相思相视无相亲,“天空是谁的春天?“当他彷徨回去时,他的堕落就不可避免了。历史兴亡之感、对他人的悲悯之情、居安思危之忧、伤春悲秋之叹,使他终其一生致力于写下深沉悲凉的情怀,让王国维判断“自北宋以来,他只是一个人”。
纳兰词虽与严小山相近,但陈维崧的《词评》说:“饮水思源,故知南唐二大家之遗风”,梁启超也说:“容若小言,追得上大家”,乍一看,他的作品犹如七宝散尽,沉重而不足,但看他的300多首诗,万种悲情汇聚,正如顾贞观所说, “人不忍心死”他也洞察到了建筑在财富世界中的影子。 “去哪里的家,都能看到山中留下的水”,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空空虚、孤独和苍凉;梁启超评论他的词“视野开阔,情感深厚”,特别是在《采桑子》中,“风亦萧萧,雨亦萧萧,鼻烟薄为又一夜”,“醒则无聊,醉则无聊,梦未至谢桥”,“有倍哀”。的确,纳兰预言了盛世的哀痛。在这一点上,他就像曹雪芹,对一个富裕家庭的崩溃深深叹了一口气,“船到江新晚了,赶上了漏洞”,除了他更早,同时作为他生命的开始,他哭了一场,感觉更有同情心——像陈子昂,谁是“我想天地,没有限制, 无休无止的和和我是孤独的,我的眼泪掉了下来”初唐时期,面对时代的开端,他们之间充满了默契的共鸣,两个人都被唤醒了。

海淀上庄永泰村位于纳兰性德展览馆北侧。
康熙十八年,25岁的纳兰驾御皇帝,游览西山农园,前往西山代嘎库奇,写下《浣溪沙代嘎库奇》:
空梁画的墙壁很冷,花雨散落在不同的日子里。香清和梵天之间没有差距。
蝴蝶从树荫下乍一看,樱桃半是鸟衔残。这时,我相对忘记了我的话。
这首诗虽不是纳兰的名作,但以情悟禅更为开阔清晰,意象既辽阔又含蓄,读来令人“悲喜交集”。他经常在西山巡游,直到近百年后,与纳兰家族关系密切的《红楼梦》作者步出白家疃至附近樱桃谷的“曹雪芹迹”。
张雅萌